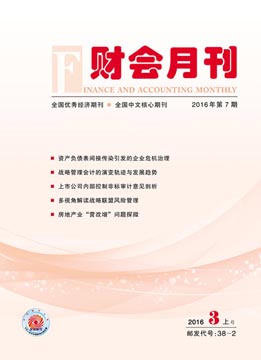【作 者】
段海艳(副教授)
【作者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河南洛阳471000
【摘 要】
【摘要】本文从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西方已有“外部董事”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其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其中,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研究包括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咨询效率以及治理效率的影响;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包括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董事任期、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外部董事声誉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关键词】外部董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咨询;董事会监督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07-0111-5外部董事是指过去或当前未在企业担任执行职务或与企业没有任何关联的董事。相对其他董事而言,外部董事未来职业的发展不受企业CEO和其他董事成员的影响,因此可以有效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近二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丑闻的频现,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改革的成效之一是美国的“外部董事占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面推行与积极推进。多个国家的政府与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外部董事数量提出强制性要求,外部董事被大量引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这种全球性公司治理改革潮流本身所暗含的假设是外部董事可以有效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那么,现实中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本文主要从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西方已有“外部董事”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经验与不足,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
监督与咨询是董事会的两大主要功能,董事会治理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董事会监督质量与咨询效率。因此,本文主要从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咨询效率以及治理效率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的影响
已有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效率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外部董事对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
就外部董事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言,Ajinkya(2005)提出并证实外部董事比例与企业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数量和质量正相关。这意味着外部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自愿披露水平和财务信息透明度,继而减少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地,Surjit(2012)提出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披露成本(如诉讼成本等),因此在研究外部董事监督企业信息披露时应当考虑诉讼成本;他还发现,企业盈余预测频率和准确性均与外部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
就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来看,Davidson(2005)以澳大利亚企业为样本,考察外部董事治理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发现使用外部董事比例衡量的董事会独立性负向影响企业盈余管理水平。Peasnell(2005)发现,在外部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经理层通过调高应计收益以确保企业利润稳定,进而避免自身收入损失的概率显著较低。Firth(2007)发现,在中国情境下外部董事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Annelies(2013)考察了外部董事对家族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家族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代理问题时,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但是,外部董事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Ching(2006)以香港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较高的董事会独立性可以降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Bradbury(2006)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外部董事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关系。(二)外部董事对董事会咨询效率的影响
外部董事除了可以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改善董事会监督效率外,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通过其他渠道无法获取的一手信息、知识和技能,并提高董事会决策质量和咨询效率。外部董事有助于企业获取行业特定知识、多元的异质性信息,并提高企业销售收入(Kor和Sundaramurthy,2009)。Kor和Misangyi (2008)考察了董事会资源(特别是行业相关经验)对新创企业的影响,发现新创企业高管的行业经验匮乏的缺陷可由具有一定行业经验的外部董事来弥补,这为那些急于摆脱资源约束的新创企业提供了解决路径。Michael(2008)基于心理学等专业知识探讨了外部董事经验与技能对群体决策效率以及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借助于在其他企业的任职经验和决策经历,外部董事可以为所任职企业提供并购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等方面的建议,并有助于提高企业并购绩效。这种积极效应在董事会相对独立于经理层的企业中尤其显著。
Francesco(2012)以意大利上市公司为例,考察了外部董事对家族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为了保证家族控制权,家族企业更多地依赖外部债务资金而非权益资金。在投资需求较高的时期,与银行有关联关系的外部董事有助于提高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此外,外部董事还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由于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高水平的,具有专有知识、技能与市场经验的人员作为支撑,而外部董事具备多元化知识与技能,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宝贵资源(Faleye et al.,2012)。Yoo和Sung(2014)提出,外部董事并不总是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而是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在股东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较大的企业,外部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效应不显著,但是,企业成长性可以逆向调节这种不利影响。对于快速成长的企业而言,外部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
(三)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
董事会由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构成。在董事能力权衡视角下,企业可以通过内外部董事比例来协调监督与咨询职能之间的关系。外部董事独立于经理层,其独立性有助于外部董事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内部董事掌握较多的企业专有信息,可以有效缓解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董事更好地行使咨询职能(Duchin et al.,2010)。企业应当根据自身对监督与咨询功能的内在需求决定内外部董事的最优组合(Adams et al.,2010;Armstrong et al.,2010)。
过于强调董事会监督职能并盲目加大外部董事比例,是否会削弱董事会咨询职能以及董事会治理效率呢?Adams和Ferreira(2007)提出,外部董事过度监督可能会破坏董事与CEO之间的信任关系,导致CEO不愿与外部董事分享战略信息,董事会咨询效率下降。董事监督与咨询是替代关系,如果董事认为自己是监督者,就会相应减少咨询功能的发挥。此外,如果董事会面临诉讼风险,董事会成员会在咨询与监督之间进行权衡,并理性选择在诉讼风险较低的监督职能上投入较多时间。Adams(2009)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过度监督会导致外部董事从经理层那里获取较少的战略信息。由于外部董事投入企业的时间、精力等很难得到CEO的认可,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Faleye(2011)探讨了过度监督对董事会监督、咨询等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多数外部董事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监督委员会任职时,董事会监督质量会得到改善,具体表现为CEO更迭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敏感性提高,经理层的超额薪酬降低,且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但是监督质量的改善是以董事会咨询职能的削弱为代价,具体表现为较低的并购绩效和较差的创新能力,并且董事会咨询职能下降的代价超出监督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进而导致董事会治理效率下降。
西方学者们普遍认可“外部董事监督与咨询不能两全”的观点。但是,Brickley和Zimmerman(2010)对这种权衡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咨询与监督职能并不是彼此孤立、可截然分离的,外部董事所掌握的信息既可以为CEO提供咨询,也可以监督CEO的业绩。外部董事为了更好地行使咨询职能,必须全方位地深入了解企业相关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而这也为监督职能的行使提供了便利。并且,外部董事的独立性有利于外部董事对经理层实施监督,也使外部董事可以从不同视角提供客观建议,进而行使咨询职能(Brickley和Zimmerman,2010)。Kim(2014)提出董事有效行使咨询职能的前提条件是对企业局限与机会等专有信息的获取,而借助这些信息,董事可以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能,约束经理层并减少经理层的私有收益。而且,外部董事任期(外部董事对企业专有信息获取水平的替代变量)与企业并购绩效、投资效率和CEO薪酬监督业绩显著正相关。因此,外部董事监督与咨询职能可以相容,且已有研究低估了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积极效应。
二、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董事会应当由具备不同技能、发挥不同功能的董事构成。根据职业背景的不同,可以将外部董事分为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
(一)CEO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由于CEO拥有特定的企业管理技能、行业经验、敏锐的商业头脑,因此相对于其他外部董事而言,他们更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善。Fich(2005)考察了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1997 ~ 1999年间外部董事任命情况,旨在揭示CEO型外部董事是否优于其他外部董事。研究发现,那些董事会独立性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多或成长性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聘请其他企业现任CEO来担任本企业的外部董事。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反应是积极的,且这种积极效应对小规模企业尤其显著。Adams和Ferreira(2007)认为,CEO基于现有职位的非同一般的权威和经验使他们可以站在专业经营和职业管理的角度对现任经理层进行监督与咨询,这是其他外部董事无法做到的。进一步地,Chan和Li(2008)提出,CEO型外部董事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那些主要由CEO型外部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对企业价值有积极影响,由CEO型外部董事占主导(占比50%及以上)的董事会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如果CEO型外部董事对董事会没有控制权,则他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不显著。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任职审计委员对企业价值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如果财务专家型董事在以CEO型外部董事占主导的审计委员会任职,则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Fahlenbrach等(2010)从CEO个人角度出发,分析CEO型外部董事的任职选择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外部董事参加同样的董事会会议、履行同样的职责,CEO型外部董事薪酬并不比其他外部董事的高。但是,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的较高需求使得CEO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机会。作为理性人,他们会选择那些可以为所投入的精力和所承担的风险带来最优回报的企业担任外部董事。但现实中,他们一般会选择规模较大、相对成熟的企业任职外部董事,以获取较高声誉和较多任命机会等间接收益。因此,资本市场对CEO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反应是积极的。
Benjamin(2014)以德国大型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监督型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如何影响所监督企业的创新活动。研究发现,CEO型外部董事对企业以专利申请数量测度的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研究将样本细分为创新型企业与非创新型企业后,发现只有创新型企业外部董事才可以对所监督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随着所任职企业技术相近程度的提高,外部董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增加。
总之,西方学者基本认可CEO型外部董事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但是,Martin和Laura(2006)提出,在其他企业担任外部董事将耗费CEO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继而有损于CEO所在企业的绩效。CEO是管理决策领域的专家使其更有可能成为其他企业外部董事的理想人选,并且CEO自身也有足够动力向经理人才市场传递这种声誉。可见,CEO型外部董事的积极作用仅限于其担任外部董事的企业,而非任职CEO的企业。
(二)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学术型外部董事在各行企业中普遍存在。Francis等(2011)发现,1998 ~ 2006年间标准普尔1500强企业中33%以上企业的董事会中有学术型外部董事。企业为何聘请学术型外部董事?
首先,企业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的目的是服务于各委员会以及监督经理层。基于对学术型外部董事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认可,他们通常被委派到各个监督委员会任职,以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董事会和监督委员会成员的财务技能是影响企业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Xie et al.,2003)。如果学术型外部董事距离企业所在地较远,缺乏行业知识或者被认为与经理层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关系时,他们作为监督者的效率将大打折扣(Audretsch和Lehmann,2006)。
其次,企业根据自身需求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目的是发挥学术型外部董事的咨询职能。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经营相对复杂的企业而言,外部董事的咨询功能尤其重要(Coles et al.,2008)。学术型外部董事可以提供外部技术或技能支持,特别是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或者信息不对称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学术型外部董事可以提供行业或企业特定的知识与信息(Anderson et al.,2011)。与这种观点类似,Audretsch和Lehmann(2006)认为,高科技企业可通过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
最后,企业任命学术型外部董事是出于对社会关系的考虑。对于新创企业、小规模企业而言,吸引关系网络较多、人脉较广的外部董事加盟,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如金融贷款、隐性知识等(Chahine和Goergen, 2013)。另外,来自于知名高校的学术型外部董事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Singh et al.,2008)。
学术型外部董事按专业类型的不同,又可分为工程技术型、财务专家型等外部董事,以下对不同类型的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展开探讨。Francis et al.(201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学术型外部董事中的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并且该影响超出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可以对企业财务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读,为经理层提供宝贵的投融资建议,甚至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等资源支持。在金融危机时期,财务专家型外部董事的资源获取功能尤其重要。
Joshua(2014)考察了企业对学术型外部董事的任命情况,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在扩大董事会规模时倾向于聘请学术型外部董事,但不同类型的学术型外部董事任命的市场反应不同。科学、医药、工程等技术领域的学术型外部董事因他们特有的专业知识得以任命,并且市场反应是积极的;管理领域的学术型外部董事因他们的关系网络得以任命,市场反应也是积极的;但是,如果他们距离所任职企业较远的话,则市场反应是消极的。
学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有些学者认为,学术型外部董事的加入提高了董事会构成的异质性,但加大了董事之间的协调成本。在董事构成异质性较高的企业,董事之间协调成本的增加可能会超出异质性带来的收益,进而导致董事会治理效率的下降(Knyazeva et al.,2013)。另外,相较于内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提供的多元化咨询建议的积极作用有限(Liu et al., 2014)。(三)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治理作用
一直以来,政府被认为是企业关键资源的提供者。企业经营的每个方面几乎都由政府规制。政府会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并通过建立准入、准出机制,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和政策补贴,或者通过立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雇佣成本等从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以及经营绩效(Schuler et al.,2002)。在国防等特殊领域,政府还可能成为企业的重要客户。既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那么不难理解企业为何想方设法与政府构建并保持良好关系。聘请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进入董事会并担任外部董事是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Hillman(2005)提出,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可以为企业提供公共政策、经营环境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与现任政府官员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沟通的渠道;同时,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合法性支持。具有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的企业财务绩效显著优于没有这类董事的企业。类似地,Kim和Lim(2010)考察了韩国1998年公司治理改革后外部董事多元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外部董事的比例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已有研究多侧重于考察政府型外部董事对企业的效果,Richard(2008)则探讨了前任政府官员成为外部董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前任政府官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深度、广度,以及随着时间推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贬值的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前因变量。
三、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
西方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外部董事任期、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董事声誉等对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展开探讨。
(一)外部董事任期的影响
外部董事有效履职的前提是对企业发展的局限与机会等专有信息的获取(Adams和Ferreira,2007)。对企业专有信息的获取可以提高外部董事对经理层的能力和工作努力程度等的认知,增强对经理层的监督并减少经理层寻租行为;有助于外部董事全方位地深入了解企业经营环境与战略定位,从而为经理层提供更好的咨询与建议。
随着外部董事任期延长,参加董事会定期会议、临时会议和各委员会会议次数的增多,外部董事获取的企业专有信息数量增加,并且可以有效缓解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外部董事个人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的经验与企业内部运营知识均会相应地增加(Castro et al.,2009)。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外部董事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建议和监督服务。此外,随着任期延长,外部董事所拥有的企业专有信息数量增加,个人经验、知识与技能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外部董事的履职意愿。因此,外部董事任期延长有助于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Kim(2014)的研究表明,外部董事任期与企业并购绩效、投资效率和CEO薪酬监督业绩显著正相关。
(二)现金薪酬与股票期权的影响
1. 现金薪酬。对经理层进行监督与咨询需要投入时间与精力。由于外部董事通常比较忙碌,进行监督的时间机会成本较高,因此需要对他们的时间投入支付较高的货币性或非货币性回报。较高的现金薪酬可以吸引声誉较高、能力较强的董事,还可以缓解外部董事的董事会会议出席率较低的问题(Adams和Ferreira,2008)。但是,较高的薪酬可能影响董事的独立性,无法有效监督经理层(Brick et al.,2006)。Vafeas(2000)发现,薪酬较高的董事对经理层的容忍度较高。Brick(2006)认为,当外部董事薪酬较高时,CEO薪酬较高,且CEO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消极影响。Ye(2014)以2002 ~ 2008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外部董事现金薪酬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发现外部董事现金薪酬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意味着现金薪酬较高的外部董事,其独立性下降,并且会威胁到外部董事对财务报告的监督效率。
2. 股票期权。Fich和Shivdasani(2005)以1997 ~ 1999年间美国财富1000强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对外部董事实施股票期权计划如何影响企业价值,发现对外部董事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市值与账面价值的比值和盈利能力较高,且对累计非正常损益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收益预测有正向修正作用。实施外部董事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非正常损益接近零,而没有实施外部董事股票期权计划的企业非正常损益为负。因此,股票期权计划有助于外部董事有效履职,继而提高企业价值。Deutsch(2007)以标准普尔1500强企业1997 ~ 2000年间的数据考察外部董事股票期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外部董事包括股票期权在内的薪酬激励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
(三)外部董事声誉的影响
Fama和Jensen(1983)提出,作为决策制定的专家,外部董事监督经理层的激励来自于对“专家声誉”的维护。当外部董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无法有效监督经理层时,他们会选择公开辞职来维护其声誉。董事声誉的价值体现在与外部董事席位相关的薪酬、股票和股票期权等财富上。David(2004)以美国1994~1996年间财富500强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价值与外部董事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企业市值增加时,会增加外部董事的个人财富,这种财富主要来自于薪酬、所有权和任职机会的增加。以任职年限为5年的外部董事为例,股东财富每增加1000美元,可以给外部董事带来11美分的财富增长,且增加财富的50%以上来自于股票或股票期权,任职机会增加带来的财富效应位居其次。
与声誉激励相对应,外部董事声誉损失则体现为董事任职机会的丧失。Fich和Shivdasani(2007)以面临股东集体诉讼的企业为样本,考察了财务欺诈对外部董事声誉的影响,发现在经历财务欺诈诉讼后,企业外部董事并不会受到非正常更迭的影响,但是外部董事任职数量会显著下降。财务欺诈平越高,外部董事所承担的监督责任越大,外部董事任职数量下降越多。Suraj(2005)以1997 ~ 2001年间发生财务重述的409家企业为样本,研究财务重述对外部董事的惩罚效应发现,外部董事受到的惩罚大部分来自于人力资本市场的声誉损失。在财务重述发生后的三年中,所有样本企业外部董事平均更迭率为33%,这些外部董事将面临巨大的声誉损失,并且可能失去在其他企业的董事席位。对于在审计委员会任职的外部董事而言,夸大的盈余水平与外部董事离职概率正相关。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的展望
现有文献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功能发挥以及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已有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地探讨。
一方面,在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研究中,学者们多使用外部董事比例作为解释变量,探讨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和咨询效率、董事会治理效率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由于董事会是群体决策,外部董事构成的异质性及其与内部董事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外部董事的治理效果,这方面的研究甚少。另外,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发挥的作用有哪些差异,哪种类型的外部董事对企业更具积极作用?处于不同行业、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不同类型外部董事的内在需求是否有差异,内在需求的不同如何进一步影响外部董事功能的发挥?已有研究侧重于考察外部董事的独立性,但是并非所有的外部董事都是独立于经理层的,那些与企业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联系的“灰色董事”,其治理效果如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值得引起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议题。
另一方面,外部董事履职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有研究探讨了外部董事任期、薪酬与股权激励、董事声誉等因素对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外部董事履职行为受到董事个人能力、履职主观意愿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已有研究过于强调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对外部董事监督效率的影响,那么除独立性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外部董事监督职能的行使?外部董事履行咨询职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CEO型外部董事、学术型外部董事和政府背景型外部董事履行监督与咨询职能时各自有哪些优势与局限?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与方法提升外部董事履职的能力?对这些方面展开探讨,对于提升外部董事治理效果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薪酬与股权激励、董事声誉会影响外部董事履职的意愿,而外部董事履职除受董事主观意愿的影响外,还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企业的性质、组织结构、股权与控制权特征、财务状况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外部董事履职的意愿?家族企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Astrachan和Shanker,2003),家族企业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已有研究多是以西方国家为背景展开的,在中国特定情境下,外部董事履职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与西方国家相比有无差异,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Dahlia Robinson,Michael Robinson,Craig Sisneros. Bankruptcy outcomes: Does the board matter?[J]. Advances in Accounting,2012(2).
Davidson R., Goodwin Stewart J., Kent P.. Internal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J].Finance,2005(2).
Eliezer M. Fich. Are some outside directors better than others?Evidence from director appointments by fortune 1000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2005(5).
Faleye O., Hoitash R., Hoitash U.. The costs of intense board monitor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1).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2).
Francesco Napoli. The board’s strategic and control tasks; family firms and their search for outside directors to support growth[J].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2012(4).
Garg S.. Venture Boards: Distinctive monitor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3(1).
Haksoon Kim,Chanwoo Lim. Diversity, outside directors and firm valuation: Korean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0(3).
Harlan Platt,Marjorie Platt. Corporate board attributes and bankruptc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2(8).
Hsin-I Chou,Hui Li,Xiangkang Yin.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istress and capital structure on the work effort of outside directors[J]. 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2010(3).
Hsu-Huei Huang,Paochung Hsu,Haider A Khan,Yun-Lin Yu. Does the appointment of an outside director increase firm value?Evidence from Taiwan[J].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2008(3).
Jagdish Pathak,Jerry Sun. Does investor protection regime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outside directorship on the board?[J].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3(4).
Jeremy A. Woods,Thomas Dalziel,Sidney L. Barton.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private family businesses: The influence of outside board members[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2012(1).